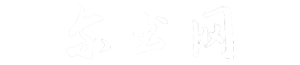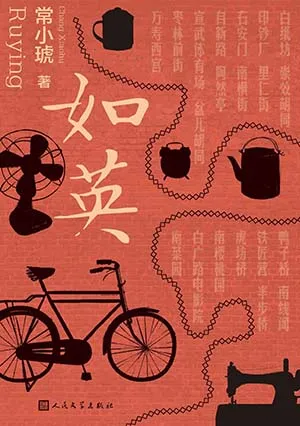
如英 內容簡介
“被家放逐的一代人”
“不知道為什麼,從佳木斯回到北京,人反而更怕冷了。”
“少平呀。”薑老蔫輕輕地喚起兒子,用手摩挲著一飛腦袋。“爸問你,你想回家嗎?”
“我想回家。”一飛用力說。“可是我叫周一飛,您怎麼糊塗啦?”
“對,姥爺糊塗了。姥爺不中用了。”
《如英》講述南城姑娘薑如英,作為“六九屆”知青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下鄉。十年後她返城回京,與同為知青的周笑走到一起。同是各自家中長兄長姐的兩人,此時卻變成大家庭內部的異類和累贅。他們還要在錯綜不定的社會變遷中彼此支撐,共同麵對外部世界的冷落與戲弄。小說以細膩溫和的筆觸,將如英周笑遭遇到的啼笑人生娓娓道來,更刻畫出北京南城人橫跨四十年的生活圖景。
在家走失——《如英》創作談
我是在白紙坊西街長大的,兒時在那裏過著無所事事又自我感覺良好的日子。直到畢業找工作,我才從白紙坊西街離開,所以說我其實和小縣城裏走出來的孩子區別不大。這也造成了我的極度晚熟,無論是哪個方麵,比如直到現在,我都認為無所事事並且能感覺到美好的日子,就是好日子。
我的小學在白紙坊西街偏東,我家住在西街偏西,每天一放學我們撒丫子就往家跑,這樣才能趕上北京台播的《聖鬥士星矢》。由於我家距離稍遠,所以每次都趕不上開頭五分鍾,所以那五分鍾裏發生了什麼,我是要等到第二天上學,在早課間聽一個叫於博奇的家夥講給我。由於我太想知道了,其他同學還總圍過來插嘴,於博奇就更來勁了,那五分鍾丫能講兩個課間,有的情節也跟我後麵看的接不上,我就懷疑丫有瞎編的成分。直到有天我使出渾身力氣往家跑,居然趕上了開篇動畫,那可是我拚命跑出來的獎勵,更重要的是於博奇知道後,他說你絕不可能趕上那五分鍾,那個距離你是到不了家的!即便我說出那五分鍾的情節,他也不信。但是對於我來說,最寶貴的是我可以不再經他講述,獨自去理解那五分鍾了。而且如同是宿命一般的,現在的我仍然在這條路上,尋找那不被人承認,不被人理解的時間。
後來我的小學搬到法源寺附近一所研究院裏,白紙坊的孩子要到當街坐公共汽車,坐到牛街南口。兩站地之外的世界,對於孩子們可稱得上遙遠,好在我們不由自主地會結伴而行,你就不會覺得害怕。直到某天早上我跑到車站,發現車來了同學卻不往上擠。我沒來及多問,用力一躥就上去了。當車門啪嘰一關,我站在鐵台階上,看到同學們都用驚恐的眼神望著我,我不知道他們怎麼了。很快,公交車到了牛街南口但沒有停的意思,而是直接開到了下一站,我兩條腿哆嗦起來。我帶著哭腔甚至是祈求著問售票員,阿姨我們這是要去哪?她愛答不理地說,禮拜寺。禮拜寺,僅僅比牛街南口多出一站,我卻覺得可能再也回不去家了。
我兩手攥緊書包背帶,擔驚受怕中雙腳落地的一刻,眼前全是留長胡須、戴白色圓帽的人。他們五官立體,穿著對襟長衫,慢悠悠地聚集在街上,邊走嘴裏邊念叨著什麼,路兩邊還擺滿我從沒見過的糕點和器物。我當然不知道那是什麼,更不知道當天是回族的古爾邦節。隻記得我仰著腦袋,獨自站在街中間,好像所有人都在看我的校服和書包,你能想象那個八歲的孩子有多絕望麼。我感覺自己進入了一個奇異國度,或者是原始部落,甚至連頭頂的樹都變得無比高大。我早已忘了學校的方向,也聽不懂他們的語言,我隻能亦步亦趨地跟在那些陌生人身後,聞著彌漫在空氣中的神秘香氣。
當我意識到周圍人的模樣逐漸正常,天變得空曠,建築物也跟著平庸起來,這才稍稍安心,我知道我走在一條正確的路上。我居然走回了學校,一進校門,大夥兒就像迎接凱旋的英雄一樣把我圍起來。於博奇說,我們以為你走丟了,我正要告訴老師你再也回不來了。我當時還講不出什麼,無法告訴他我去哪了,看到了什麼。但他說的沒錯,我確實走丟了,至於我是怎麼回來的,為什麼沒有受到傷害,我把它歸結為某種神跡。
那時我和表弟常去印鈔廠裏洗澡,倆人誰都不願負責裝毛巾肥皂的塑料筐。那是個淺綠色的塑料筐,有兩個提手,拎久了還剌手。於是我們想出個絕妙的主意,一人提塑料筐的一個提手去印鈔廠洗澡。那真是個讓人大開眼界的場景,每到周末,兩個禿小子一人攥著塑料筐的一邊,以同樣的步伐,並肩走在廠區裏,大兵們見了都要多看幾眼。由於表弟高,我個頭矮,所以塑料筐裏麵的肥皂和毛巾總會掉出來,有次掉的是一大瓶蜂花洗發液,砸我腳麵了,生疼。
帶著深深的滿足感,我們洗完澡,總要站在澡堂門口吹涼風。我告訴表弟,一人拿著一邊塑料筐提手實在太丟人了,不如來時我提,回去你提。表弟說行。很快他發現,這樣明顯自己吃虧了,因為我們進廠時直奔澡堂,但是洗完出來,總要在廠區裏亂竄。我們要爬樹,要品嚐花壇裏的一串紅花蕊,要在幹涸的泳池裏扮演聖鬥士,或者在警衛連的兵營裏,和那幫大兵摔跤。那也是我最神氣的時候,而表弟無論幹什麼都要提著個裝肥皂毛巾的塑料筐,跟在我左右。每當他也想爬樹,也想玩雙杠,或者從泳池跳台上往池底看的時候,我都會提醒他,你,別忘了拿好塑料筐。
他終於明白過味兒了,提出拿塑料筐的順序應該變一變,但是我提醒他,別忘了誰是哥哥。有時我們玩的時間遠比洗澡還要長,甚至天都黑了,他累得恨不能把塑料筐掛在脖子上,他有幾次還故意扔到地上,踢了幾腳。直到有一天,不僅來的時候是我提塑料筐,洗完澡我也主動拿筐,因為我帶了個照相機出來。
暮色降臨,廠區的地下管道在檢修,我們不得不繞路。沿著一排迂曲的遊廊,聞著被翻起的土地和鬆樹混淆出的濕氣,我們走到從未去過的印鈔車間,那是真正印鈔票的工作區。我們似乎感受到了某種威懾力,不僅身體發冷,還有了尿意。走到高聳入雲的虎皮色水塔下麵,眼前已接近一片昏黑,隻能聽到淩亂的涼鞋聲。
“給我看看照相機唄,讓我按兩下。”表弟說。“我幫你拿塑料筐。”
我說那可不行,雖然這是一部傻瓜相機,但是裏麵有著寶貴的交卷,按兩下可貴了。又走了一段路後,我說天已經全黑了,如果想拍出人影,需要用閃光燈,我告訴他,電池可貴了。表弟不再說話,雖然他比我高,脾氣也比我差,但是他沉默了。我這個人就是心太軟,隻好答應他等到走出廠區,我們就在大門口拍照,那裏有很亮的燈。我們一人按一下,也不廢電池。
可是我們越走越不認路,這才明白印鈔廠太大了。我們能聽到奇怪的鳥叫,還有那座標誌性的德式鍾樓,“咣咣當當”響個沒完。
“八點了!”我們看著彼此,認真數著。
後來我們終於走出廠區,不過是朝著家的反方向,一直走到了大觀園的南門。
“能拍照了嗎?”表弟問我。我們確實需要慶祝一下,至少看到大馬路了。
我仰起頭,看著麵前那塊刻著“補天遺”的巨石,決定我們在這下麵給對方拍一張。我正指揮表弟,怎麼借助月光拍照片,卻聽到身後有人朝這邊說話。
“你們這樣可不行。”
是個大人,個子不高,但是個大人。我記得他的臉很白,眼窩深陷,雙眉濃重,聲音有些沙啞,而且還穿著一身黑衣。我和表弟早嚇得不知該說什麼。
“給我看看。”他伸手向我們要相機。看著他那副認真樣,我真後悔為什麼帶相機出來。我覺得如果交給他,一定會被搶走。終於我還是從表弟手中拿回相機,交給了他,這時表弟緊緊貼住那人身邊,我覺得他隨時都能搶走。
然而那人看了看卻樂了,他說你們沒開鏡頭蓋呢!表弟看向我,我還死死盯著我的相機。隨後那人拿出紙條,用筆在上麵寫了一串文字。
“這是我的店,你們要是真想學攝影,來這裏找我。”他對我們笑著。
當我確認他是把紙條和相機一起還回來後,我和表弟撒丫子就跑,我的涼鞋都跑到腳跟後麵去了。
那幾乎是我第一次與外部社會產生某種聯係。雖然紙條早就扔了,可後來我總在想,他為什麼要叫住我們,還讓我們找他。直到長大以後,我還是會想,他應該知道我們太小,是不可能去找他學攝影吧。在某個夜晚,願意給兩個傻孩子寫電話,願意和他們聊聊攝影的人,可能他也在尋找自己的路吧。
我再一次走失,正是麵對著家門口,那時我已經懂事了。但我還是弄不懂,自小便在姥姥家長大的我,怎麼忽然進不去家門了。我看著姥姥在當街喊,聽你媽的話,回你自己家去吧。我看著她的臉,卻聽不懂她的話。即使在我後來最無助的時候,我依然被拒之門外,但因為我的晚熟,對這個家裏發生了什麼自然一無所知。那似乎隻是告訴我,你該長大了。印鈔廠的保安把我攆出來,姥姥家的親人把我攆出來,可是我沒有長大。
當我搬離白紙坊,我舉著那個傻瓜相機,對準自己家的每一個成員——床、沙發、書架、電視機、折疊桌和醬油瓶以及肥皂盒,我對準每一個角落,毫不吝惜地按下快門,並且全程打開了閃光燈(可想而知洗印出的照片和作案現場一樣)。我想把這裏的一切放大後印在心裏,為此我甚至對著每一個房間跪下磕頭。但我依然一次次地回來,像個孤魂野鬼似的在這條街上遊蕩,可是我沒有長大。
至今我還保留著這個陋習——總要把白紙坊那一帶走上幾圈。我無數次經過和表弟打鬧的巷子,經過槐樹下姥姥家的窗前,經過富麗堂皇的印鈔廠大門,仿佛是在一遍又一遍地證明,我沒有長大。至今我還是對無窮無盡的窗子感興趣,對黃昏日暮時,映照著萬家燈火的窗子感興趣。那些如夢似幻的光線向我轉達著,人們吃飯時在談論著什麼,或者為了什麼感到憂愁。你可以從外麵輕鬆走過一棟塔樓或是一片幽深的院落,但是幾平米的房間內卻是某人的整個世界。擺放在書桌上的物品次序,牆壁上的水漬和熏黑印記,茶幾與扶手椅上的木紋,以及混淆在客廳裏煤煙和潮氣,窗子裏的神秘世界永遠吸引且阻止著我。
所以不斷地了解和探索白紙坊,成為令我著迷的事。我讀奧茲的《愛與黑暗的故事》,讀王鼎鈞的《昨天的雲》,看他們以赤子之心去寫兒時的感受和夢境,去追溯父母輩那令人心碎的過去,他們平靜又坦誠的文字令我也有了書寫《如英》的念頭,或者說令我意識到,從很久以前我就注定要寫這本書了。對於白紙坊,對於父母的人生,對於那些家庭內部的不解之謎,我抱有著太久的幻想。於是在長達三年的訪談中,要以寫作的名義與父母交流,我才知道他們是“六九屆”知青,才真正知道我是知青的孩子,才知道他們對過去的苦難與不甘守口如瓶,造就了我的晚熟。於是,我便這樣開啟了一場回到過去的探秘之旅。
正是由於極度晚熟,我無法去相信自己的記憶和判斷。我隻能向他們反複追問過去的人與事,追問那些細節、動機和各種可能,我隻能相信他們。直到母親在我麵前抽噎落淚,直到父親沉默不語,我才意識到自己在撥動的傷疤有多深。我的父母,或者說那一代人,從未真正地融入過這個社會環境。他們永遠活在一種不合時宜的處境中,用盡全力也無法弄懂這一切,無法讓自己被人接受,無法獲得尊嚴。他們是被家放逐的一代人,被家詛咒的一代人。我在兒時看到的很多事情,很多選擇,以及很多問題,隨之也都有了答案。
於是我知道了我的晚熟、我的堅忍、我的憤世嫉俗,我的自私、我的狡猾、我的反複無常,這些是從哪而來的基因。我也知道了他們是我永遠逃離不掉的底色。但他們與我不同,他們從未想過重回白紙坊,那裏是他們的傷心地,或者說,家便是他們的傷心地。我的追問一度也激起他們對我的反問,令他們向我尋求答案。我仿佛看到他們始終也沒有走出那片傷心地,仿佛看到的全是無望的答案。
即便如此,寫《如英》的過程艱難卻也幸福。那段日子裏,我不僅可以回到八九十年代的白紙坊,還可以與從前身邊的人重見。尤其是他們在一起時,不曾說過的話,我在這本書裏幫他們說了。他們錯過的人,我在書裏讓他們再度相逢。那些無法化解的誤會與遺憾,我在書裏替他們解釋了。至於他們永遠走失的那個家,我也在這本書裏,幫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回去。
當我聽到這些傷害過我父母的人說,“那都是時代造成的錯”,我為他們感到可悲。我覺得苦難與記憶不該分成三六九等,高低貴賤。也許你認為某些人一生的追求或者難以觸碰的痛苦,是過於渺小甚至荒謬的,某些人的人生是簡單到不可理喻的。但是誰又能界定,多大的苦難才是苦難,多複雜的人生,才叫人生呢。我認為即便是令孩子傷心的小事,即便是時代造就的無數重複的苦難,但它降臨到個人頭上,都不能因為渺小或者重複,就不值一提,就可以刪除。
理解苦難,書寫記憶,是不是一個小說家的必要素質?我不知道。我倒是看到太多人很會利用機會展示自己,在被許可後的台子上,奮力地舞弄著他的沉默,我為此感到羞恥。這樣無聊的小說家,我也不懂寫作的各類流派和主義,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小說家,我覺得這種純粹的認識問題非常無聊。我可以什麼都不是,我可以永遠做一個在家走失的孩子。
如英 作者簡介
常小琥,1984年生於北京。已出版長篇小說《琴腔》《收山》等,中短篇小說見《當代》《收獲》《十月》《北京文學》《上海文學》等刊,同時參與過多種影視劇本創作。曾獲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、“紫金·人民文學之星”小說佳作獎、華語青年作家獎、《上海文學》中篇小說獎、《北京文學》年度優秀作品獎等。